
曾繁田:孔子的一些范畴,比如天、道、仁,都能够充满悲剧感、命运感乃至历史感,为什么到了理就稀薄了?刚才张先生谈到佛教的影响,理的这种状况和对于静的追求有关吗?
张祥龙:是,印度的思想方式与中国的思想方式毕竟有些不一样。印度的宗教和哲学有它极高深、极精微的方面,但是也有它自身的特点,比如你刚才说的静。他们追求一个某种意义上是脱开了现实世界和实际生活的高妙境界,或者叫作梵,或者叫作佛性,等等。
并且他们认为,要追求终极的真理就要离开家,这在印度是一个整体的传统,不光是佛教,印度教也是这样。当然印度教也有入世的一面,青年时期要享受人生,壮年要成就事业,但是到了老年,他们也主张要离开家庭,到森林中去反思、苦修,认为这样才能得到人生最终的意义。佛教那就更是如此了。
就这种离开家庭的倾向来说,至少从先秦儒家的角度来看,是有重大缺陷的。但是秦汉以后佛家在中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思想上的魅力自不用说,佛教确实能够讲出一套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道理,并且富于终极性;从现实生活来看,经过南北朝、五代的乱世,百姓非常痛苦,不堪重负,而佛家的观念恰能够帮助人们摆脱忧苦。同时,那时候的人们对儒家的理解已经比较贫乏了,觉得儒家只在现实层面,不够精妙,不够根本,尤其是个人的终极追求得不到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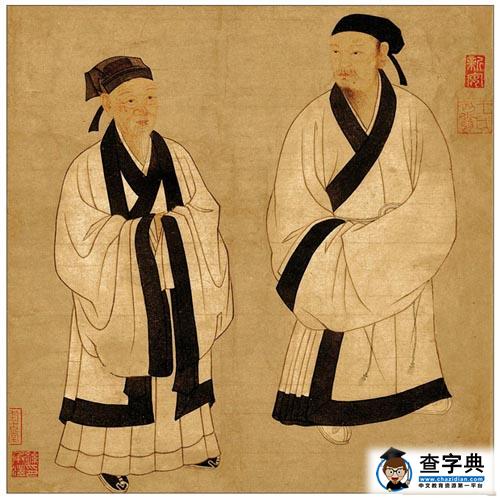
而佛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我感到有形无形就在这方面,他们追求静,追求一个不变的本体和天理的世界,这方面可能稍有一点走偏,虽然他们也强调理离了气是不行的,但是毕竟理在气先。对于理和气的关系,朱子辨析良久,哪边也不愿意丢,但最终还是理更根本,理更重要。这是有重大思想后果的,在很多地方都体现出来了。
儒家到了理学这里,获得了一个新的形态,表面上变得高深了,能够跟佛家打个平手。 就像现在西学进来,如果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出一套可以应对西学的东西,大家就觉得很了不起,我们也有高深的妙理。可是,理学确实为此付出了代价。我感到在周敦颐那里路子还比较正,但已经有这个苗头,从程颐往后就更明显了。其实大程还是很愿意把情、理打通,但是没有办法,整个时代的思潮不可逆转,儒家要建立新的范式,能够与佛家的范式相抗衡,他们觉得只能如此。这样付出的代价确实挺大,像刚才我们谈到的,孔子身上最吸引人(至少是最吸引我)的那些方面,确实有所削弱。
曾繁田:张先生常讲感觉直观、范畴直观、本质直观。此三种观照方式,在《论语》的记述当中是否有所涉及?
张祥龙:这样一些直观,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现象学讲得比较多。牟宗三先生有一本书谈智的直观(牟先生谓之智的直觉),他是从康德的角度讲。智的直观这个思路,在康德那里是被禁止的,他认为人不可能有这种直观。但是牟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哲理中就有这种智的直观。可是现象学,恰恰谈出了本质直观。感觉直观或感知直观谁都承认, 是吧,传统的西方哲学一直讲:感觉或感知是一种直观,而理智不是直观,它是对感觉材料的加工。但是现象学用直观打通了感知和理智(甚至理性),所以能够讲本质直观或范畴直观。这对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化、两分化的思维方法,是一个重要突破。
我感到《论语》里面也有本质直观,当然不像胡塞尔讲的那么僵死。胡塞尔讲的本质直观虽然有重大突破,但还是比较僵硬。孔子的思想方法肯定不是概念抽象,也不是辩证法, 也不是逻辑推演,等等,都不是。我的恩师贺麟先生(贺麟,19021992,着名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他学贯中西,创建新心学,是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谈宋儒的思想方法。他说宋儒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直觉法,讲得非常精当。他把直觉法放到了理智的后面,那就是后理智的,而不是前理智的。 前理智的直觉光是有所感悟,但是说不出来,也不想去说,没有自觉的思想在里头。像是一个践行的人,有活泼的、原本的认知,但是他没有充分的反思,他没有意识到什么,也没有表达出什么。
理智的反思,能够对之前的实践活动加以反思,但是它在事情过去以后才进行,我叫它冷反思。而贺先生讲的后理智的直观,它能够当场做出直观,同时里面是有反思的,我叫它热反思,它是当场的思考。贺先生这个讲法当时对我很有启发,他讲陆象山的直观、朱子的直观,各是什么意思。我感觉在孔子那里,直观就更微妙了,我愿意把它称为情时直观。情,是一种至情;时,是一种艺术化的时机,儒家以六艺帮助我们领会这个时机。起于至情,发乎时中,就是这样一种情时直观。

在人生之中,这种情时直观几乎无处不在,只是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它的哲理含义。 一位母亲在荒野中生了一个婴儿,她对这个孩子的那种慈爱,里面有没有直观呢,有没有时呢?这位母亲不用人手把手地教,她就能够知道怎样去照顾自己的孩子。什么时候该喂奶,她不用特别去学,她对孩子的爱里面,就已经含有这个时了,她照顾自己的孩子,与孩子同喜同悲。这种情时直观,可以比之于西方哲学中舍勒讲的情感直观伦理直观,但是还更微妙得多。因为舍勒所讲的情感中的道德直观还缺少时这一层,不是完全缺少,但是毕竟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论语》里面,这种情时直观体现得很多,我在课堂上和文章里做过许多具体的分析。比如《学而篇》一开篇孔子就讲到学而时习之,里边的时就不止于时常,而有时中时机化的意思,也就是在你的所学将忘又还未全忘之时, 将要离有入无之际,这时你习之,则必悦乎。再比如《里仁篇》孔子讲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里边的孝意,就体现在一喜一惧对交互补之同时里。
孝是人的天然的情感,但孝并不是现成的,并不是说,我想对父母好我就一定能对父母好。孝里面一定有时,真正的孝子,既发自内心地爱父母,也有时的智慧。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曾子的父亲打他,他不跑,他把自己对父亲的爱、敬、顺,给规则化了。孔子知道以后,大怒。如果不跑,要是让父亲把自己打死了,父亲就犯下了杀子之过。最后曾子也醒悟过来,如果父亲拿大杖打,就一定要跑,如果父亲拿个小棍儿打,就不应该跑。所以,孝不是规则化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境有所变化。儒家学《易》,恰恰是把我们原本的爱,用最合乎时机的方式实现出来。
这样的例子《论语》里面太多了。比如正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从来不像苏格拉底那样要下一个定义。在孔子那里,君是什么,君就是你要像个君,父是什么,父就是你要像个父。再比如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不谈这些吗,他谈仁谈得少吗,非也,他总是在具体的情境里面来谈。这甚至和后来孟子、荀子的讨论方式就很不一样了。当然孟子有许多地方也保持了这种风格,孟子也讲权,不知权,就没达到儒家的高境界。荀子相对来说就比较理智化,但是他也有许多出色的地方。 所以我感到,如果读《论语》的方法得当,就能看出其中精微的哲理韵味,而不像后人认为的那样,《论语》只是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在教育上和道德上的言论,避开最有哲理的性与天道等问题不讲。尤其到黑格尔那里,他就认为孔子所讲的那些只不过是缺少概念的世俗智慧,哪里都有,因为他自己用的是概念化的辩证方法。可是我们看《论语》《中庸》《易传》等经典里记载的孔子的话,那真是充满了哲理韵味。这样的思想最能够抵制哲理上的观念形而上学化,或把宗教的人格神实体化,而它同时又不失去哲学追求原初意义的那种眼力和宗教达到神圣性的那种究极能力。
新闻网站: